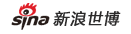城市打工90后青年认真耕耘自己未来
四
采访中,一些漂泊在城市打工的90后青年说,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方向,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他们曾期待在城市里书写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却发现现实如同一个无垠沙漠,将他们深埋其中。
2010年春节,贵州省织金县阿弓镇金鱼村黄洁一家少了几分节日的喜庆,四口人沉浸在对未来的迷茫和担忧中。黄洁的哥哥刚从贵阳打工回来,因为工资太少和个性的原因,黄洁的哥哥决定不再离乡务工。黄洁觉得哥哥的决定让自己的压力更重了,“家里收入又少了一块,我读书又正需要钱,所以很心疼爸爸妈妈。”黄洁说。
初中毕业那年,尽管黄洁成绩出色,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让黄洁读高中上大学,她只能选择了一所中专院校,学习旅游管理。中专每年1500元钱的学费,对于黄洁家而言,意味着要忍痛杀掉一两头猪。每个月,当黄洁收到父母寄来的400元生活费时,心里总是想着爸妈在家俭用省吃的场景。400元的生活费,对于1993年出生的花季少女而言,装饰青春的靓丽成为了不切实际的奢望。“不经常买衣服,大概两三个月才买一件吧。”黄洁说。在就读的中专院校中,生活朴素的黄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该校教师陈芊说:“我们学校生源比较复杂,有的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好,有的就相反。像黄洁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里压力是比较大的。”
黄洁确实承载着巨大压力,刚刚读完一个学期的她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她想早点毕业,然后当一名导游,给家里挣钱。“我希望早点毕业,早点赚钱,不要再让我的父母操劳,让他们早点享福。”黄洁语气认真地说,去城市打工成为了她和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途径。
在我们的叙述中,17岁的黄洁似乎显得有些突兀。世博园里的小白菜,家境殷实的林洋洋、梁佳伟和彭媛媛,还有姚贝尔、吴青雯和章子渊……这群90后的青春脸庞各有特色,追求着丰富多彩的梦想。但是,似乎从出生那天起,黄洁的梦想和未来就显得简单而纯粹,要工作,要挣钱,要在茫茫人海的城市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或者说安身的小窝,要通过工作来拯救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在我们的叙述中,黄洁可能是突兀的,但对于中国千千万万名90后而言,她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的普通一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迅猛发展的,还有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数据显示,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同样截止到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59.27%、23.36%和17.37%,东部地区比重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
发展的不均衡,迫使着中西部劳动力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在2008年前后,那些熟悉的务工者形象开始有了变化——来自中西部的90后开始大量涌向东部城市,成为了务工群体中的一股新生力量。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这些90后务工者称作“新生代农民工”。
来自云南洱源县的董艳青今年刚满19岁,但却已经有了在昆明、广州和嘉兴的务工经历。每一次跳槽,董艳青都将原因归结为“工资太少,根本不够花”。董艳青平时喜欢上网,尤其是在QQ上认识新朋友,畅谈人生百态,加上每个月的伙食费和烟钱,700来元钱的工资确实不够。2009年董艳青在多次向家人抱怨工资太少后,辞了昆明的药店工作,拿着母亲给的路费南下广州。在广州,人生地不熟的他最终找了个超市售货员的行当营生,没干两个月他又听朋友的介绍去了嘉兴。目前,董艳青正在嘉兴一个工厂工作,每个月收入不足1200元。
在聊天过程中,董艳青特别问了几次诸如“哪个城市工作工资高,什么行业待遇好”的问题,他计划在月底辞了工厂的工作,北上北京去找找机会。家里人不同意董艳青继续在外面漂泊,务工两年来董艳青不曾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却向母亲讨要了五六千元钱。在云南农村,这笔钱甚至是一个家庭两三年的收入。董艳青的父母还有很多理由要求他回去:他的亲弟因为高中读书压力大,患上了忧郁症,休学在家;他的父母日渐年长,无力独自耕种家里的几亩农田。但是董艳青不愿意回去,城里的生活让他迷醉,他喜欢上网,喜欢吃麦当劳,喜欢逛街。他说他要留在城市,尽管只有中专学历。
采访中,许多漂泊在城市打工的90后青年说,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方向,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他们曾期待在城市里书写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却发现现实如同一个无垠沙漠,将他们深埋其中。
其实,看不到方向和未来的,又岂止是深埋于工厂中的90后一代。时光回溯至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如吹皱一池春水一般,这篇对人生发问的文章迅速引发了一场涉及全国的公共讨论。我们在此选摘几段文字,如下: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
这封署名“潘晓”的信出自当年的两个青年黄晓菊和潘祎之手,信里,黄晓菊和潘祎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并最后发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
2010年6月,坐在我们面前的黄晓菊,比起年轻时略有发福,但眉宇间仍能看到几分“潘晓式”的生动和深刻。1980年,25岁的黄晓菊在街道一家羊毛衫厂工作,这还是“被照顾”进去的。“我当时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不能骑车不能走路,父母远在内蒙古,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外祖父去世了,我必须得自己赚钱治病,否则就有残疾的危险。”于是心高气傲的黄晓菊硬着头皮给街道写信,请求“无论如何给安排一份工作”。
“进去才知道,那家街道工厂,除了退休老人,就是像我类似情况的年轻人,小儿麻痹症、病的……一个月十几元钱虽然可以自己治病吃药了,可心情怎么会好呢?”黄晓菊在工厂里做的是最机械化的活儿——缝补羊毛衫,干活的时候,她的手在动作,可心却飞扬了:“我还那么年轻,难道就一辈子这样了吗?”
如果黄晓菊不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也许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可她偏偏喜欢文学和哲学,她总善于从中提炼人的终极意义,却在联系自己时,满脑迷惘。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酝酿在青年中发起一场讨论。编辑部当时收到了很多信,都是青年诉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女编辑马丽珍就考虑把讨论主题从“讲实惠”、“一切向钱看”转移到人生观上面来。她和另一位编辑马笑冬开始奔忙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黄晓菊就是在座谈会上被《中国青年》的编辑马笑冬发现的,“我这人天生表达能力强,那位编辑觉得我挺能说。”
那几次座谈,让黄晓菊惊觉:“每个人都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但都不满意,比如有些人还在农村插队,他们就困惑,为什么有些人就有各种渠道回来呢?到底是应该扎根农村还是应该回呢?我这才知道,原来烦的不是我一个人啊,我还以为自己有病呢……”
后来,看了黄晓菊8000多字的稿子,马笑冬惊呆了,她尤其被“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那段惊得目瞪口呆。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是原文,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是年5月1日,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大讨论由此展开,前后共收到了六万多件读者来信。汹涌而来的信件证明,潘晓的惶惑并非仅限于黄潘两人,潘晓的惶惑其实是整个上世纪70年代人的惶惑。
潘晓的困惑已经过去了30年,但即便是在今天,阅读完潘晓困惑的我们才发现,这样的焦虑和担忧几乎也存在于如今的青年人身上。2010年6月,中国青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副所长邓希泉坦言:“青年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对成人世界和青年世界割裂和交锋的问题,这是所有的青年在成长阶段感到迷惑、寻找答案。就像很多经典的读物能够感动一代代人,就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永恒的问题,这种话题并不一定给你答案,但一直都在讨论,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给予不同的形式和答案。”
30年前,正是因为有了“潘晓讨论”,中国青年们在沟通、交流和探讨中度过了自己的焦虑青春。邓希泉相信,与成长有关的讨论和思考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是否有潘晓这样的人物,因为青年的成长不会停息。“青年会永恒地面临与成人世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交叉,怎样适应社会,怎样解决个人对人生的迷惑,怎样构建一个更好地去理解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人生、社会、世界的价值……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认识得好了,他可能会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如果认识得不好,那可能会选择流落在底层。这些核心的东西,任何时代只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有差别。”
成长总会经历风雨,但风雨之后的阳光依旧灿烂。何曦梁早就把在城市里发迹的愿望抛在脑后,19岁的他来自汕尾,目前正在东莞一家工厂做管理员。每到轮休的时候,何曦梁都会跑跑职业介绍所和招聘会,闲时上网也会经常浏览一下招聘信息。“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工作是能提供培训的,这样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何曦梁说。因为家里父母都有社会保险,何曦梁没有给家里寄钱的压力,他希望能在工作中增加阅历,“将来如果无法留在城市,就回家乡找点事情做”。
来自广西的廖婉怡也在东莞工作,每月工资1500元。廖婉怡喜欢把钱攒起来,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回家乡开家服装店。每次上街,廖婉怡都会特别关注服装店的布置、选址和货品等等,虽然她很少给自己添新衣服。来自安徽的胡晓薇刚满18岁,正在上海一家理发店做学徒,她也希望能从师傅那里学得一手美发的手艺,认认真真耕耘自己的未来。
社会也在帮助这些涌向城市追逐梦想的90后。2010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同年6月7日,广东省出台政策,为农民工迁入城镇户籍开辟了新的方案。知道这个消息后,何曦梁说自己会更加努力工作,增加自己的能力,争取能够留在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