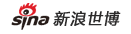伦敦零碳案例馆:城市中心农庄不仅是园艺表演
本报记者 沈轶伦
这几天,到上海出差的英国人托马斯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在伦敦市中心的菜田。每日与在英国的妻子电邮加摄像头频频沟通,唯恐他的洋葱和莴苣会枯萎。
托马斯的这块田学名“配额地”,是由伦敦市政府出租给居民自行耕种的公用地。
伦敦市中心成了“大菜园”
伦敦“都市种植”项目,田地就在伦敦市中心。比如托马斯的菜圃,离他的住宅区只有步行两分钟距离,年租金约12英镑。由于全伦敦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4300人,托马斯足足等候了3年才获准使用这块约6平方米的田地。
在世博园伦敦零碳案例馆,“伦敦是个大菜园”就成为展示的主题之一。伦敦市长提出,到2012年增加2012个新的种植空间。屋顶、废弃建筑工地、公园、被忽视的住宅角落都会被改造成社区菜园。英国内河航道还免费提供了运河边的土地,而且在驳船上建造了流动菜园。甚至连伦敦交通局也正在将铁路两旁的土地改造成菜地。
从农村走进闹市,这样的都市菜园不仅伦敦有,也同样出现在美国洛杉矶的主要街区,甚至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前的空地都成了市民耕耘收菜的好去处。
为什么要在城里种农作物
在都市耕种其实并非新鲜事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便呼吁所有西方人在自家花园耕种,实现自给自足以支撑战争胜利。当时英国国王则身体力行带领英国人民耕种“胜利花园”。如果说当时在市中心开垦农田是为了应对战时缺衣少粮的境遇,那么如今的“开荒南野际”则代表着都市人对绿色有机食品的渴求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托马斯最初申请菜园,就是因为他想让家人吃上有机蔬菜和水果,但是英国有机蔬菜价格昂贵。权衡之下,他选择了“种”。如今,他种植的芝麻菜和埃及香菜都成为妻子做色拉时的首选,“吃亲手种植的蔬菜,那种乐趣难以用语言描述”。
在满足口腹之欲后,种植为托马斯带来了意外收获。因为菜园就在市中心,许多居民会在散步的时候停下来看他种田,互相聊天,久而久之大家成为了朋友,“我是苏格兰人,在伦敦居住多年,有时连邻居都不认识,但菜园给了我们交流的平台。”
和托马斯一样,在亲近田园的过程中,种植者渐渐看重的不是收成本身,而是渴望由此活动寻找到生活本源。在洛杉矶散落着70余处社区菜园,种植者坦言:“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我们本来彼此保持戒备,但在菜园里一起工作,学会了互相扶持帮助。”在世博园温哥华案例馆,工作人员也历数都市种菜的好处 “不仅让温哥华变得更加绿色,而且减少了车辆往返运送蔬果的频率,间接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截至去年年底,温哥华全市登记注册的社区菜园已达2029个。
如何实现城市规范种田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海有不少种田爱好者,一些小区业主种菜之余还养上鸡鸭。但由于涉嫌侵占公共绿地,加上邻里纠纷不断,不管是种在小区空地还是自家花园里的“社区菜园”被全面叫停。
既然都市种田有诸多好处,为何在上海却频频遇阻?许多种菜爱好者坦言,肥料和水源问题,成为了引发矛盾的主要导火索。一些市民为了给菜地找天然肥料,常到小区附近的化粪池“取材”,或在自家痰盂罐里沤肥,阵阵恶臭引发邻居强烈抗议。还有一个小区的业主为灌溉菜蔬竟然挖井取水。
实际上,在“都市种植”推广过程中,来自政府的因势利导从未缺席。伦敦“配额地”在分配给市民前明确规定是用于种植植物或饲养家禽,申请者认领后必须立即使用,每年政府会派人到各个菜园检查每户的使用情况,疏于耕种或处置不当的地主会被开除出菜园,交由其他申请者使用。为了避开化肥、杀虫剂污染等问题,种植者一般采用液体海藻当化肥,用大蒜驱赶蚜虫,用糖水引开鼻涕虫,尽量使用无化肥种植方法实现培育纯天然植物。
在温哥华,市政府在政府官网设立专门网页,随时更新菜园空缺的情况以及介绍菜园适合种植何种花草蔬菜。一些申请到菜园的市民不急着种菜种瓜,而是种上了绿草花卉。城市由此有了让社区老人和孩子免费休憩、娱乐的场所,街道和十字路口也变得更为美丽。温哥华推广城市菜园计划的工作人员介绍,建设这些菜园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推动市民参与,“要让市民感到他们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
|
|
|
|